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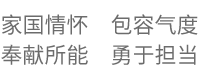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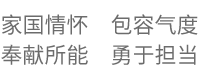
(文:智合藤 采访:智合藤、智合橘子)
你的人生往往不取决于你收获了什么,而是取决于你放弃了什么。纵观梅雷的经历,这话显得尤为贴切。梅雷15岁就读吉林大学少年班,于1996年出国读硕,一边读物理,一边自费学计算机工程。毕业后就职于财富200强的Office Depot公司,3年后已任高位的他弃IT从法,转身去念杜克大学的J.D。本以为飞翰可以成为他实现理想之地,没料到梅在2009年离开飞翰,创业成立了美科律师事务所。于一场337调查案确立在国内的知名度,于一次上诉代理赢得美国同行的尊重,于众多的放弃中凝练成自己理想的生活,这是梅雷,一个从未想过给别人打工的温州人。本期智合专访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律师如何创业,并取得客户信任的故事,更多的是希望从梅雷律师的经历中看到选择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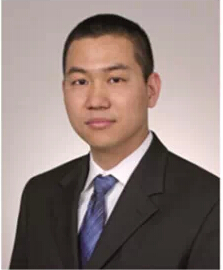
天才少年转身学法,弃$10万年薪从未悔
笑称自己不是“学霸”的梅雷15岁考上吉林大学少年班。虽然自己并不太喜欢物理这个被分配的专业,但考虑到读物理在当时拿美国签证非常不易的情况下颇具优势,选择继续攻读物理。出国读研时,梅雷一边靠奖学金的资助读物理,一边自费读计算机工程。“当然读计算机只是一个过渡,因为我知道在美国读计算机好找工作,我那时的想法是之后再去读个MBA,从商。”
智合:那为什么之后又学了法律?是对法学有特别的兴趣?
梅雷:倒也说不上是特别的兴趣。原先是想去读MBA,后来正巧认识了一个美国律师,觉得法律还蛮有趣,就打消了去考GMAT读MBA的念头。考虑到从商并非要专门去学校学习,在实践过程中就可以学。(当然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幼稚,但当时的确这么认为。)但法律若没有经过系统训练,肯定是学不会的。所以想先去学个法律,至于以后具体做什么,以后再说。
智合:但事实是,您那时在OfficeDepot公司已经做到了高层,辞职之后再去学法律,这对一般人而言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从你的描述来看,感觉并没有纠结。
梅雷:确实,那时候我在Office Depot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了。离开的时候,老板和所有的美国同事都很吃惊,觉得我疯了,这么好的工作不要。我当时的位置相对比较独特,更多的是做沟通的角色,比如跟全球不同子公司的经理们交谈,看他们对电子商务有何需求,设计方案后,把需求转化成程序员所能理解的逻辑表示出来。因为有的时候程序员和商业人士之间沟通不顺畅,所以我充当中间人。最后走的时候,我的上司和美国同事都觉得给我的薪水已经很高了(10万美元),当时即使哈佛耶鲁毕业的律师在佛罗里达的起薪也就只有10万。所以他们就说你去读法学,首先机会成本浪费了三年,然后又交了这么多学费,毕业以后薪水也差不了太多。你为什么要去读法学?但那时候我才24岁,不想在Office Depot待一辈子,一眼就看到尽头。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就工作强度来讲,在Office Depot可能会轻松很多,去读一个MBA,有可能会不同的路。但是每条路都不错,现在走了第二条也从未后悔。
智合:您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了飞翰?当时您其实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首选飞翰?
梅雷:因为我之前已经有比较多的工作经历了,不觉得一定要去大所,这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美国大所吸引人的主要原因在于高薪。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一路都比较顺利,所以对钱并不看重。在Office Depot之前我还在一家电信公司做过编程和商务方面的业务,考虑若再读个法律,自己日后可以开个咨询公司(其实和现在的律所也差不多,现在律所也有很多咨询业务)。即使去大所,我的目的也比较直接,努力学习,但是肯定不会留在那里做合伙人。
美国大所分工非常细,知识产权这一块也会细分,比如做专利申请和专利诉讼会在不同的团队。我在法学一年级暑假在一家大所实习后就已经意识到我对证券业务不是特别喜欢。而知识产权和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有关,会更合适我。飞翰更偏向综合性,并没有像别的所那样有很多明显的划分,专利申请、许可、专利诉讼都可以学。我进入飞翰以后是以做专利诉讼为主,特别是337调查。我知道我以后肯定会离开,所以也刻意去学习专利撰写和申请,也尝试学习政府合同、许可、专利池等业务。
从未想过给别人打工的温州人
梅雷说自己从未想过要给他人打工,包括之前在公司、飞翰他知道都只是暂时的。看的出,梅骨子里始终流淌着温州人创业和开拓的血液,种种创业过程中的艰难也只化为几句轻描淡写。
智合:从您刚才的描述,您创业的想法很早就有了?什么时候开始的?
梅雷:可能好多温州人从来没想过给别人打工。我这个想法已经酝酿很久了,后来意识到如果再不离开大所的话很可能就离不开了。因为你在大所待得越久,就越舍不得离开,尤其是快升为合伙人的时候。这种叫Golden Handcuffs,也就是金手铐,因为它会用钱把你铐住,你赚的钱越多就越舍不得离开大所,所以我在2009年初就决定辞职自己创业。
智合:当时你一个人走的,没有后顾之忧吗?
梅雷:我2009年离开飞翰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金融危机。不过飞翰对我倒很好,他们表示说什么时候我都可以回去。这一点我非常感激飞翰,至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不行的话就再回去。一开始别人都很难理解,觉得我在飞翰收入高而且业绩不错,为什么还想走。
智合:为什么选择在2009年创业?当时的经济环境似乎并不理想。
梅雷:我在飞翰的老板也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在这么差的经济形势之下创业。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很多人创业是因为被裁员,被迫创业,而我却比较独特。不过后来才发现09年离开飞翰去创业,却是最好的机会。原因在于那时候全美的大所高端业务受冲击,很多优秀的美国律师愿意出来寻找更好的机会。一般美国人对个人的发展更加看重,一旦发现他没有更多机会,你即使给他很多钱,他也不一定会留下。因为时间很宝贵,他要去追求更好的机会去体现他的价值。所以当年的金融危机有利于我组建新的团队,招聘到了几个很优秀的美国律师。
智合:听说您创业一开始就租了非常好的办公室?这怎么考虑的?
梅雷:对的,很多小所开始的时候一般都在家里工作的,美国比较流行这种virtual office(虚拟办公室)。但是我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特区最繁华的地段租了办公室,很多朋友都很吃惊,“没有任何客户你怎么去做这些?”但我离开的时候就觉得要做就要做高端的律师,不可能把办公室设在郊区或者是virtual office。客户如果过来或者是要见面,我们必须与自己想创立的品牌有相应匹配的办公环境。
智合:刚开始创业有没有特别艰难?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梅雷:困难肯定有,事实上一开始(从飞翰出来)我就做好两年之内没有任何客户的打算。不过我们运气很好,从第三个月就开始有了盈利。最早只有两个人,一年以后有4个律师,但我们做诉讼的话必须是团队操作,一般都是三到五个律师做一个案子,所以我们必须得扩大队伍。但发现2011年的时候,根本招不到优秀的律师,所以我们推掉了很多业务。客户当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团队的成员。你没有很好的团队成员,客户给你活,你又做不好,那你不仅会丢掉客户,也会坏掉名声。所以那时因为人手不够,就推掉了很多案子。
后来我们采取的方案就是,付的薪水比一般的中小型所高很多(比大所略低一点)的同时,允许我们的律师更自由的工作,在家上班也可以。比如我们有一个女律师,她当时有了孩子,想白天在家上班,有客户时再过来,但是有些大所不给她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诸多限制。而我们可以,既给她更多的自由,同时也给她留办公室,这样才比大所更有吸引力。
智合:您刚才提到您3个月就开始盈利了,是怎样找的客户?
梅雷:这和美国法律媒体Law360有些关系,一开始我有时间会写法律文章(当然也是兴趣),我写了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文章发表在Law360上,引起了一些大公司法务的关注。之后就有一些公司法务联系我,我就飞过去和他们见面。当他们看到我们律师很多是从飞翰出来的律师,且都是名校的高材生,就逐渐地给我们一些工作。就在同时,我们也打赢了代理的一个中国公司的案件,通过海关规避贸易壁垒。这个国内很多媒体都有报道。还有一个是337调查上诉案的成功。可以说没有这三件事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从海关壁垒看律师如何赢得客户信任
梅雷很谦虚地把前一两年的顺利归功于运气,事实却远非如此。若非几年前开始就对中国企业遭遇337调查案的持续关注,若非积极尝试采用新的解决方式给被诉企业出谋划策,若非每个案子都在思考客户真正的需求,短时间内要赢得客户信任也只能是天方夜谭。那些只关注个案胜诉率的律师,还真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智合: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谈一下那件让您在国内名声大噪的案子,温州三蒙科技的海关壁垒案。您刚创业就接到这么个大案子,怎么做到的?
梅雷:海关的这个案子说起来很有趣,但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代理的。事实上我在飞翰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这几家企业(幕后都是温州老板)在美国受到337调查,成为被告。作为中国人,尤其是温州人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事。在飞翰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联系过,结果他们没有理我们。后来当我离开飞翰时,发现他们当初的案子都已经判决了,且输的一塌糊涂。又因这几家中国企业之间有竞争关系,所以他们都单独请了律师,根据媒体报道,每家企业花了将近三百到六百万美元打官司。
后来我们给中国败诉的这四家公司发过传真,询问他们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法律建议。我那时建议他们尝试下美国海关的程序。但是那时美国的海关程序基本上是空白,所有人(即使很多美国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海关的程序法非常独特,我们自己当时也是在摸索中,即使在飞翰我也没做过这一块业务。我们发传真的四家,有三家都打过337调查,他们说美国的那些大型律师事务所从来都没有告诉他们海关程序,怀疑我们是骗子,就没有理睬我们。倒是他们中的第四家,四家中最小的一家——三蒙科技,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愿意尝试一下,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当时的价格也很便宜,具体律师费大概收了不到5万美金,相当于花5万美元解决了三百万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当时我就告诉他,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决以后,被判侵权的旧产品已经无法被海关改判,因为海关只是执法机构,没法改判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但是海关可以鉴定和判决规避设计产品是否侵权。
海关的鉴定程序的法律依据是非常独特的海关程序法。美国海关总署在华盛顿特区,下面设置了很多部门,我们都不知道哪个部门受理规避产品是否侵权的鉴定。我们当时打了很多电话,终于有个部门告知我们说他们受理这个案件。那时候可以算是现学现卖,海关总署的工作人员告知我们相关程序法法条,并提醒我们递交文书的时候要符合这里面的法条。两个月后海关直接判决我们客户的产品不侵权。
智合:这个判决非常有利,想必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梅雷:对的,此判决书一出来,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这个判决以后,美国的经销商都不敢买别的公司的产品(因为别的公司被判侵权后没有走海关判决的程序),都跑过来买我们客户的产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判决还挽救了三蒙科技的几百个员工的工作。原先三蒙科技官司输了后公司停产,员工都准备回家了。海关的判定一出,他们就不需要(回家)了。
智合:这场战役之后,其他三家有都来找您吗?
梅雷:那也没有。因为每家公司都已经聘请了不同的律师。但是有几家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打电话过来问我们海关程序怎么走,我们还是毫无保留的教他们的。跟很多人不一样,我非常愿意分享经验。如果其他律师多走海关程序的话,海关执法程序也会因此变得更完善,而这块业务量也会越来越大,对大家都有利。我们欢迎同仁的竞争,因为案件做好做坏具体还是要看做的过程的细节,而不是靠垄断知识。
智合:就应对扣押的问题,以及遭遇337调查,走海关程序算是您的首创,之后大家都走这条路了?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做?
梅雷:在我们之后很多案件都走了海关程序。手机行业如HTC,彩电行业如VIZIO(美国一家大的彩电品牌)等公司均采用了此种方法。海关程序现在就变得很流行了,成为了一个规避贸易壁垒(尤其是337调查)的一个常用法律途径。
后来我想清楚了,为什么之前很多大所都不愿意用海关程序,原因很简单,律师费太低。大所没有必要去做这一业务。一般来说,大所代理337调查案件,赢了OK,输了再上诉。或者客户有新设计的规避产品,自己可以宣称不侵权,直接去卖,海关也不一定会扣留(但是如果海关扣留,公司出货时又与对方都有协议,迟延履行了,这个赔偿就很厉害,而经销商也就不敢再从你那里买货物了)。之前337调查拿到不利裁决后,要么什么程序都不走退出市场,要么上诉,要么回到国际贸易委员会,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鉴定规避设计产品是否侵权。但是鉴定程序律师费非常贵,至少一百来万美元。基本上客户就这几种选择。
所以我们那时提出这个海关方案,就相当于开辟了一条“物美价廉”的新路。我们现在代理被调查客户的时候,和一般律所不一样的是,我们会考虑更多。虽然我们律所代表的中国公司在337调查案中胜诉率很高(中国公司总体败诉率很高并且很多律所从没有代表中国公司胜诉过),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每一个案件一定获胜。
智合:在面对此类诉讼案件时,您一般会做哪些考虑?
每次我们打官司时候都会问自己,万一输掉怎么办?——在打官司初期就要做好这一步的规划,因为你不能再等到败诉后再上诉。就像三蒙科技,后来虽然还是上诉了,要把名声打回来,但是很多公司在上诉过程中就倒闭了,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如果这是它们唯一的产品的话,它们不可能等两年的上诉过程。若最终赢了官司,输了市场也是输。我们代理客户的目的就是怎么保护他们的市场,即使输掉了的话,如果我们两个月能让他们的新产品进入美国的话,那对他们来说还是赢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会给客户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各种各样的部署,布置很多道防线(包括专利局的复审程序)。
因为如果337调查万一输掉了,对方也许还会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告你侵权并请求赔偿(337调查败诉的结果只是禁令没有赔偿)。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程序的时间差,结合多方面的法律途径,想策略。很多律所接手案件时都会宣传他们的胜诉率很高,但却没想过万一输了怎么办。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没有给予客户最好的服务。律师必须要有个大局观,不能总是局限于某一个案子,这样埋头办案的律师很多,但是能站在更高的层次替客户考虑的律师就相对较少了。
海马不是马,荷兰猪不是猪
对梅雷来说,创业初期第三件大事,是替三蒙科技打的上诉案。“正如海马不是马,荷兰猪不是猪,用户负载终端也不是负载终端。”这个论点说服了法官,而这一次胜诉,梅雷被国内媒体称为“首位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出庭并胜诉的华人律师”,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出庭赢得了美国同行的尊重与认可。
智合:能分享一下那个让您名声大噪的案子——关于GFCI的337调查上诉案的具体细节吗?国内媒体对您的评价很高。这是第一家中国企业在败诉并上诉后获得改判的案例。
梅雷:那个案子还蛮有趣的,我进入这块领域(337调查)的时候,事实上“车轮战”都已经打了五六年了。三蒙科技看到我们将海关程序打赢了,老总的信心来了,继续委托我们做337调查的上诉,因为他认为自己旧的产品也没有侵权。上诉的时间相对比较漫长,经历一年半后才判决。
这个案子比较经典,联邦上诉法庭中三个法官,两个对我们投了赞成票,一个投了反对票,最后直接改判不侵权。一般上级法院判决都会采取发回下级法院重审的方式,而我们的案子中,上诉法院直接就判决我们客户不侵权。
这个案子一审并非我们代理,上诉时我们拿到案子后,看了十几万页文件发现一个突破点,在于负载端(load terminal)和用户负载端(user load terminal)的区别。国际贸易委员会法官一审和委员会复审时都将用户负载端视为一种负载端,而且从纯技术角度考虑,用户负载端可以解释成一种负载端。但是我们是法律人,而非技术人员。
我们在对专利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专利说明书解释实施例时,每次都将用户负载端和负载端单独分开解释,而且都作为不同的零部件进行解释,在图里面都有不同的标识。因为专利并不仅仅是技术文件,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法律文件,所以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我们根据专利撰写的这个漏洞,认为从法律上无法将用户负载端与负载端归为一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虽然这个想法之前的代理律师也已经提出两次,但都在国际贸易委员会那边败诉。因此,我们花了更多心思考虑如何打赢这官司,在写上诉文书时,我们采用更多法律上的论点去解释专利文件是法律文书,在权利要求解释的法律框架下去阐述这两个并非同一个概念,即在本专利中用户负载端不是一个负载端。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因为大部分法官没有技术背景,他们更多的是在乎你的理由是不是合理(make sense)。如果我们向法官提出,从法律角度说明用户负载端并不是负载端,但是因为语言上很相似,法官很可能会先入为主认为我们讲的不合情理,不会静下心来听我们如何具体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无法打消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话,不管我们在法律上的辩论多么全面,我们很有可能会败诉。
翻来覆去考虑了好几周后,我终于从心理学的角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想到了一个通俗的排比在法庭上陈述,“正如海马不是马,荷兰猪不是猪,用户负载终端也不是负载终端。”
后来一开庭就对三个法官说:“我知道这两个词名字听起来很像,但是你们不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考虑它们是同样的东西,就像海马不是马,荷兰猪不是猪,这两个也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仔细评估这是不是一个同样的东西。”结果我们在三个法官之中成功说服了两个法官,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
这个上诉的胜诉对我们在美国律师界的地位有重要作用。因为当初有四个大所代理四家中国客户,有三家都提出上诉。所以在开庭时有很多人在旁听,包括很多美国大所的大牌律师,后来我们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下面反映不一。有的觉得有道理,有的不以为然。后来案子判下来我们胜诉后,有些美国律师在别的场合上碰到还会说:“那个难度这么高的案子居然也被你打赢了,你居然提出这样的观点!”
后来我们每次在案件中提出新的观点的时候,会得到很多美国同行的尊重,他们会认真地听我们的观点,期待一些独特的、他们并没想到的法律点。而之前他们却可能会认为华人律师只会拉中国业务,对疑难的法律问题不会研究得十分透彻。如果没有那案子,可能我们不会这么快赢得同行的尊重。
美国的337调查,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智合:中国企业到美国去会遇到很多贸易壁垒,如337调查,那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呢?
梅雷: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必须要做好一个综合的规划。中国企业在设计产品的过程中就要考虑专利布局和规避设计。但是有一些标准性的专利你可能规避不了,或者规避难度很大,或者你认为你已经规避了,对方有可能还会来告你。一旦进入诉讼,中国公司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诉讼成本。即使有些案子中国公司是可以打赢的,但是它没有钱,请不起律师,花不了几百万美元去打官司,它也被迫放弃应诉。为什么中国公司放弃应诉率这么高?就有这样的问题。
而且应诉以后就要像我所说的,你要综合考虑,万一败诉了怎么办?你产品和市场怎么能保护住?如果技术规避不了的话,要不要走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无效程序?因为在国际贸易委员会无效专利的难度很大,但是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无效难度就会低很多。因为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法官都有专业技术背景,判无效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而且无效的法律标准也不一样。联邦地区法庭或国际贸易委员会做专利无效抗辩,它首先默认专利有效,无效的标准是“确切和令人信服(clear and convincing)”的标准(一般认为无效证据要达到90%以上的无效可能性),就是说你得有非常强大的证据证明专利是无效的。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不一样了,首先没有默认专利有效,只要你能证明超过50%的可能性这个专利是无效的,美国专利商标局就会判专利无效。而且对权力要求的解释,美国专利商标局也会解释得更广一点,更有利于无效。所以要综合考虑,要看每家被告公司产品规避设计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要看专利的有效性有多大。
关于平衡、选择以及对年轻人的建议
智合:您做律师非常忙,但做义务律师或者义务授课等事项并未落下,您怎么平衡时间?
梅雷:这没有办法,大家都很忙,大所小所都一样。律师工作时间都很长。但是如果只做你自己这一块活的话你就得不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你要回报社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像我一直参加美国亚裔律师协会的活动,帮助奥巴马竞选总统等等。此外,我还做一些律师援助的案件,跟知识产权没有直接关系,如代理非洲难民的政治避难案,艾滋病患者的维权案等等。我觉得参与这些事是一种社会责任,也能更接地气一点。美国教育也一直教育大家要对社会有回报,有一种责任感。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在美国,律师援助弱势群体是挺常见的。
智合:最后想请问下梅律师,有没有对现在25岁到30岁阶段的年轻人提点建议,对照您自己的经历。
梅雷:25岁我还在读法学院,之后去飞翰工作。首先,每个人必须要搞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要去律师事务所,也可能做公司法务或其它工作。选择了这个行业以后,肯定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兴趣是动力的前提。其次,一定要努力工作。聪明人我见过的简直多得不得了,然而最成功的却不一定是最聪明的,而是最努力的人。因为努力很重要。努力是指两点,一是工作时间,在一堆聪明人里面,一般很难再比别人更聪明,但做事可以更努力更仔细,也就意味着更多投入。奥巴马竞选总统时都这么仔细,我们更加要做的仔细。二是你的态度,即使有些比较枯燥的事情,如果你的态度端正,资深的律师也能看到。正如扫地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慢慢地,你的上司会知道你做事是很认真很仔细的。当然,专业知识也要不停巩固。因为认真努力工作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很聪明,实力比较接近。如果你本身实力比别人差,那更加需要弥补。
读书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要总是算计什么课程以后对自己有用或者没用,因为很多知识可以融会贯通。即使法律也一样,有不同的学科,尽量把每一门课学好。学生的工作就是学习,要尽量使自己学更多东西。
另外,我建议新律师不要太局限在自己工作的范围,要接触不同的人,因为很多法律是融会贯通的。我有一个朋友原来是商标律师,两年以后改行去做公司上市业务,现在在美国做得非常成功。我问她怎么能拿到机会的,其实也是因为她出去跟不同人接触,让别人意识到她自身的个人素质,才拿到改行做公司上市业务的机会。对年轻律师来说,跨行比较容易,等你有了一定经验了以后,跨行成本太高。所以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要只会埋头苦干,多参加社会活动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
另外,我也建议年轻律师多出去参加一下社会公益活动,多做法律援助,这样容易培养人文关怀,况且我们本来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就像我给非洲难民做政治避难法律援助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是对人性的理解。某些非洲难民,如果被遣送回国必死无疑,每次我们的胜诉就是挽救了客户一家人的生命,所以代理案件时有很大的使命感。因为我们平常主要是给公司做法律服务,有时候就会缺乏这种人文关怀。所以我们时刻意识到如果我们打赢了官司,客户就保住了市场,员工就不会丢掉饭碗,特别还有每当我们帮中国客户打赢一个官司,就会慢慢的改善中国及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形象,所以我们珍惜每个案件,以最大的努力和热情工作。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做公司业务的律师,也应该尽量人性化的工作,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